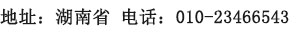明朝正德年间,邯郸府有个少年名叫冯淼,早年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姐妹,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和老仆冯忠在一块过日子。若论冯淼的相貌,真可说面如傅粉,眉清目秀。论学问,可算得满腹经纶,能诗善赋。
他为人风流倜傥,慷慨好施,只是也有两个不足之处,那就是恃才傲物、好酒贪杯。尽管人们争着拿文章给他评阅,没见他夸过一声好字。尽管人们争着给他作媒,没见他赞过谁家小姐。既是谁家小姐他都不中意,也就只好过独身的日子了。终日放歌纵酒,作诗填词,自命为当世之谪仙。
一天清早,冯淼骑着驴到郊外游逛。将近正午,觉得有些累了,就下了驴,在路旁一棵大树下歇息。背靠着大树,闭上眼睛,推敲着诗句。正在悠然自得的时候,猛然听见一阵紧促的铃声和蹄声。睁眼一看,两匹黑色的小驴倏地紧贴着自己身边闪了过去,登时尘土飞扬,呛得他连连咳嗽。
冯淼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禁不住大喊了一声:“喂!”想叫住骑驴的人,跟他们讲讲理。那两匹驴跑过去约有十几步,停了下来,骑驴的人也回过头来。冯淼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个女子。看穿着打扮,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鬟。
不知怎么的,冯淼的目光一时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般,盯在那小姐脸上,不能移动分毫。本来是满面怒容,刹那间竟变得和颜悦色。人家站住了,冯淼却不知说什么好了。
那女子见冯淼不说话,便微微点了点头,看样子是表示歉意。然后,转身加了一鞭,两匹小驴一阵风似的跑得不见了。
冯淼呆在那里,眼睛直盯着那人影消失的地方。半晌,才清醒过来,赞叹了一声:“真是倾国倾城啊!”继而又想:这是谁家的小姐?想来想去也没个头绪,只得长叹一声,再也没有郊游的兴致了。回到城里,走进一家酒楼,喝了个酩酊大醉,就歪在那里睡着了。直到黄昏时候,才微微有些清醒,骑上驴往家走。
回家途中,路经一座破庙,山门前长满了荒草,围墙大半坍塌了。就在冯淼从门口经过的时候,那山门“呀”的一声开了,走出一个人来。冯淼漫不经心地用眼一瞥,不料竟是骑驴的那位小姐。那小姐一眼看见冯淼,马上退了回去,关上了庙门。
冯淼的一颗心禁不住狂跳起来,又一想:怪呀!这位小姐怎么会住在这座破庙里呢?当时他醉醺醺地也顾不了许多,拴上了驴,顺墙豁子跨了进去。见里面到处是砖头瓦块,遍地是乱草蓬蒿,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
正在徘徊时,忽然看见一个衣帽整洁,须发斑白的老者走了过来,问:“先生从哪儿来呀?”
冯淼忙说:“偶然从这儿经过,想进来瞻仰瞻仰。老先生也是来此瞻仰的吗?”
“哎!我是外地人,带着家小来到此地,还没有租到房子,只好暂时在这儿住下。既然先生光临,就请到屋里喝杯茶吧!”于是,老者领着冯淼穿过大殿,走到殿后一个跨院里。
一进这个跨院,就像到了另一个地方。中间一条石径扫得干干净净,不见一根荒草,两旁有几株垂柳,长条摇曳,婀娜多姿。冯淼被领进北面一排正房,室内香气扑鼻,布置得十分雅致。宾主坐定之后,彼此问起姓名来。
老者说他姓辛,名叫蒙叟。冯淼本是为那骑驴的小姐而来,这时又是酒意未消,也就不揣冒昧地说:“小生今天两次巧遇女公子,不胜倾慕。倘若女公子尚未许配人家,小生意欲毛遂自荐,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
老者看了看冯淼,笑着说:“女儿的终身大事,老汉不能擅自作主,还得和拙荆商量商量。”
冯淼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请老者给他笔砚,当即写了一首绝句:“玉杵千金觅,殷勤手自将。云英如有意,亲为捣玄霜。”
(诗的内容是表示求婚。唐人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裴航路经蓝桥驿,向一个老妇人求浆水喝,老妇命一少女捧浆而出。少女名叫云英,非常美丽,裴航想娶她为妻。
老妇说:“我有神仙给的药,要用玉杵白去捣,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你能用玉杵白做聘礼,捣药一百天,我就把云英许你为妻。”
裴航果然求得玉杵白。和云英成婚后,两人吃了灵药都成了仙。玄霜是丹药名。)
老者看了诗,笑着把它交给一个小丫头,拿到里屋去了。一会儿,那丫头走了出来,在老者耳旁悄悄说了几句。老者站起身来,说:“老汉告便,请先生等一会儿。”说罢,也进了里屋。冯淼隐约听见他在里面说了几句话,便又见他回到外面来。心想,大概这亲事成了。
没想到老者坐下以后,竟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根本不往这件亲事上说。冯淼实在忍不住了,就问:“小生求亲的事,老先生到底心意如何?可否对小生直说呢?”
“先生是本府有名的才子,我早已闻名,不过有些事我很难对您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只要老人家同意,我什么都能答应,一切都不计较!”
“老汉有十九个女儿,有十二个已经嫁了出去。不论哪个女儿的婚事,全由拙荆作主,老汉是从不参与的。”
冯淼—听他有那么多女儿,忙说:“我求的是白天带着丫鬟骑驴出门的那位小姐。”老者听了也不答腔。于是两下里默然相对,事情僵到那儿了。
这时,冯淼听见里屋门帘后面窸窸窣窣有女人环飒的声音。冯淼借酒撒疯,突然跑过去,一掀帘子,说:“娶不到娇妻,让我先看看也是好的。”果然自己的心上人正站在帘后,这时,羞容满面,张皇失措地跑了。
老者见冯淼这样无礼,勃然大怒,说:“你这畜生,太放肆了!来人,给我轰出去!”立即拥上来几个人,扭胳膀揪脖领把冯淼拉到门外,推倒在地上。
冯淼双手抱头,迷迷糊糊地,只觉得浑身挨了不少砖头瓦块,幸好伤的不重。待了一会儿,觉得没有动静了,抬头一看,山门已经紧紧地关上了,自己那匹驴子还在门边吃草。只好爬起来,跨上驴背,垂头丧气地往家走。
谁知道由于心里只想着辛家小姐,走迷了路。四下一看,不知怎么走进了深山幽谷。这时已是深夜,树上夜猫子在叫,远处一声接一声的狼嚎,吓得他毛骨悚然,不知如何是好。在焦急中,忽然看见远方树丛中一闪一闪地似乎有灯光,心想那边可能有人家,便狠狠打了驴子几鞭,直奔有灯光的地方。
跑到近前一看,原来竟是个很大的宅院。冯淼连忙敲门。就听里面有人问:“半夜三更的,是谁叫们哪?”
冯淼赶紧大声说:“我是走迷了路的,行个方便吧!”
里面的人说:“等我回禀一声。”冯淼只好在门外等着,唯恐主人不肯接纳。
一会儿,听到开锁的声音,接着,黑漆大门向两下敞开。一个年轻的仆人出来,说:“主人有请。”说罢,一面替冯淼牵驴,一面引着冯淼进去。冯淼被引入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一个中年妇人出来问了冯淼的姓名和籍贯,便到后面去了。
待了一会儿,就听有人喊:“大夫人出堂!”就见门,帘一掀,几个丫鬟簇拥着一个白发如银,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出来。冯淼慌忙起身下拜。老夫人说:“少礼!请坐。”宾主坐定后,老夫人上下一打量冯淼,说:“你是冯云子的孙子吧?”
冯淼觉得奇怪,心想,这老夫人是怎么知道的,忙说:“是的。老夫人怎么知道?”
老夫人笑着说:“咱们是一家人哪!你父亲冯浩是我的外甥。老身风烛残年,一向在家修真养性,长期不走亲戚了,你大约就不知道有我这门亲戚吧?”
冯淼听老夫人这样一说,忙说:“我幼年的时候,先父就故去了。所以先祖的亲友我大都不认识,没有来往,望您老人家指教。”
老夫人呵呵一笑;说:“我不用细说了,你回去好好想想!自然就知道了。”冯淼也就不敢再往下问。老夫人又问:“你怎么半夜三更跑到这深山幽谷里来了呢?”
冯淼就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楚。老夫人一听,哈哈大笑,说:“有你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婿,还能辱没谁家?这个野狐狸精把身价抬得也太高了!孩子你别发愁,我把她给你叫来。”冯淼一听,老夫人好大的口气呀!虽是疑信参半,也连忙拜谢。
老夫人扭头对丫鬟们说:“我还真不知道辛家的姑娘有这么漂亮呢!”
一个丫鬟说:“他家有十九个姑娘,个个长得都那么好看,不知小官人说的是哪一个?”
冯淼说:“看样子也就十七八岁。”
那丫鬟说:“十七八岁——那准是十四娘了。老夫人,您就忘了,三月间,她不是还跟着她娘给您来拜寿了吗?”
老夫人想起来了,说:“啊——就是那个穿莲花瓣鞋,蒙着头纱的吧?”
丫鬟齐声说:“对,就是她。”
老夫人笑着点了点头,说:“不错,那丫头可真会打扮,长得也真美。”转过面来,对冯淼说:“你这孩子,眼力不错呀!”说着又回头对丫鬟说:“派人去把她叫来。”
丫鬟答应一声下去了,一会儿的工夫就回来了,说:“辛家十四娘来了。”
紧跟着,一个红衣少女翩然而入,跪在老夫人面前。老夫人连忙把她拉起来,说:“唉!以后你就是我家的媳妇了,不用像丫鬟们一样行这样的大礼啦!”
那辛十四娘低声答应说:“是。”
老夫人慈祥地看着她,用手给她理理鬓发,又捻捻她的耳环,像哄小孩似的问:“十四娘,这些日子在家都干什么呀?”
十四娘轻声说:“闲了,就绣绣花。”
说话的时候,无意地用眼睛一扫,正好看见冯淼,那白得透亮的两颊立刻泛上了一阵红晕,显得局促不安起来。老夫人说:“你见过他吧?这是我外甥的儿子,人家一片痴情要跟你结为夫妇,你怎么这样捉弄他,让他半夜三更到山里来看狼啊?”
十四娘答不上来,羞得连耳根子都红了。老夫人呵呵地乐了一阵,说:“我叫你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给你作媒呀!告诉我,你乐意吗?”
十四娘低着头,悄悄向冯淼和老夫人扫了一眼,迟疑着不说话。老夫人拉着她的手,一再追问:“说呀!你乐意吗?”
十四娘微微点了点头。老夫人乐了,当即吩咐说:“给他们收拾一间房子。我今夜就让他们喝交杯酒。”
十四娘急得手足无措,赶忙说:“太夫人,婢子还得回去禀告爹娘呢!”
“呃,我给你作媒人,还能出什么错吗?”
“太夫人的主意,我爹娘自然不敢违抗,可是这样草草了事,婢子是死也不敢从命的。”
老夫人一听,不但没生气,反而更高兴了,说:“这小丫头,心里有准主意,真是我们家的好媳妇。”说罢,就从十四娘发髻上摘下一朵金花,交给冯淼,作为信物。冯淼也摘下腰间系着的一个玉牌交给十四娘。
老夫人又叫人拿过皇历来,翻了翻,说:“后天就是好日子,你在家把一切准备停当,我派人把新娘子给你送去。但有一样,可不要惊动街坊四邻哪!”
这时,远方传来一声鸡叫。老夫人立即打发人送冯淼出去。仆人把冯淼的驴牵了过来,冯淼出了门,见东方已经发白。他跨上了驴背再回头看时,哪里还有什么宅院,分明是一片黑森森的松林,林中有个大坟。
冯淼走过去一看,石碑上刻着薛尚书及夫人张氏之墓。冯淼想起薛尚书正是祖母的胞弟,他的夫人张氏是父亲的舅母。这么一想,知道自己方才是遇见了*,但却毫不害怕。心里想:那么十四娘也是*吗?冯淼一面寻路回家,一面想着这件事,总也想不出个究竟,不知不觉又走到那座破庙门前。
这时,天已大亮,冯淼心想,我到底要问个明白。于是推门进去,穿过大殿,直奔眼后的跨院。谁知院子里面目全非。虽然仍有一条石径,却长满了一尺多深的荒草,那北面的一排房,墙倒了三面,遍地是碎砖、朽木和泥皮。冯淼在庙里转了一圈,就没看见一间能住人的屋子,也不见一个人影。
走出庙门,跟附近的住家一打听,都说这庙有三四十年没人管了,庙里尽是狐狸。冯淼心里想:难道那辛十四娘会是狐狸?想到这儿,十四娘那娇羞的样子便又浮现在眼前,自言自语说:“这样的绝代佳人,就是狐狸,我也要和她白头到老!”
冯淼回到家里,立即让老仆冯忠打扫房子,准备办喜事。到了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
清早起来,冯淼就穿好了大红吉服,等着十四娘到来。谁想等了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总不见十四娘来。直到天黑,还是不见踪影。冯淼心里痛苦万分,渐渐地不抱什么希望了。心想,*狐的事情,迷离惴恍,能有什么凭据,算它是一场春梦吧!想是这样想,可是那十四娘的影子却始终在眼前徘徊。
鼓打三更,冯淼还没有丝毫睡意,坐在书案旁边,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这时,忽然门外人声嘈杂。冯淼慌忙跑去把大门打开。
只见一辆油壁香车停在门前,两个俊俏的丫鬟搀扶着天仙般的十四娘下车进了屋。后面两个披着长发的家人抬进一个圆墩墩的像个大瓮似的东西来,放在堂屋门后边。冯淼仔细一看,竟是个大闷葫芦罐儿,比平时小孩子攒钱用的闷葫芦罐儿要大几十倍。别的什么嫁妆都没有。安顿了一下,送亲的人便都回去了,只留下一个叫香宜的丫鬟在这儿服侍十四娘。
洞房中,冯淼问十四娘:“我那舅祖母张氏不过是个女*,你为什么对她那样服服帖帖?”
十四娘毫不隐讳,说:“薛尚书现在当了五都巡环使,方圆几百里的*狐都是他的随从,夫人的话谁敢不听啊!”
冯淼这才知道十四娘果然是狐仙。心里不但没有疑惧,反而更加锺爱。想到舅祖母为自己撮合的恩德,第二天便备了一份祭礼,到薛尚书墓前祭奠了一番。
回到家里,忽见两个身穿青衣的仆人拿着锦缎两匹,前来贺喜。也没说话,把贴着红签儿的锦缎放在桌上,就告辞走了。
冯淼看看那红签儿上也没有落下款,不知是谁家的贺礼。正想追出去问,十四娘把他喊住,看了看锦缎,说:“别问了,这是舅祖母的贺礼。”
冯淼和十四娘郎才女貌,新婚之乐自不用说。
再说这邯郸府有位公子名叫楚景春,父亲官居通*使,权势极大。这楚景春自己不学无术,却好附庸风雅。因为冯淼是本城才子,所以经常和冯淼往来。他听说冯淼娶了媳妇,便带着一份厚礼前来祝贺。冯淼留他在家吃了饭。
过了两天,他又下请帖请冯淼到他家赴宴。十四娘知道了,就对冯淼说:“那天楚公子来贺喜,我在门帘后面偷偷地看了他一眼。这人长得鹰鼻子鹖眼,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能跟他来往,不然要吃亏的,你不要去了。”冯淼本来就瞧不起这种俗人,听十四娘一说,就真的没有去赴约。
不料,第二天,楚景春竟找上门来。还没进屋,在院子里就嚷嚷起来,说,“淼兄,你好大的架子呀!我是来兴帅问罪的。”一面嚷着一面进了屋,说:“昨天你太不赏脸了,我请了许多客人作陪,不想你这主要的客人没到,你想我有多尴尬?你认罚不认!”
冯淼只好说:“实在抱歉,昨天我身患小恙,所以……我认罚,认罚!”
楚景春说:“你认罚就行,老实对你说吧,昨天请你赴宴是因为我最近作了几首诗,自觉颇有太白的风骨。你是我们当世之谪仙,我想请你当着大家品评一番。遗憾的是你竟然没来,现在我把诗带来了,请你斧正,就算对你的惩罚吧!”说着,就拿出自己的诗集来,翻开了一页,用手指着说:“请看这几首。”把诗集递给冯淼后,扬扬自得地静候人家称赞。
冯淼不得已,只好看下去。见第一首题为《游春》。下面写着:“红花紫一片,芳草绿如麻,谁说春光坏,打掉大门牙!”
冯淼实在忍俊不住,“卟哧”一声,笑了出来。一面笑一面连声说:“好诗,好诗!”
楚景春以为冯淼真的夸他,说:“不想拙作能令当今谪仙绝倒,不胜欣慰之至!”
听他这一说,冯淼更是笑得流出了眼泪。楚景春还一再要冯淼加以品评,其实不过是想让人家多夸赞几句。冯淼被逼不过,笑着说:“老兄非要我品评,可要恕我直言哪!”
“当然,当然。”
“我赠你六个字的批语:‘高山滚鼓之音’。”
楚景春不明白这六个字的意思,心想自然是句赞美的话,忙说:“过奖,过奖!不过这句话的出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是出自《论语》吧?”
“哪里是出自《论语》。是出自《冯子家语》!”
楚最春还没明白冯淼是在取笑他,怕人笑话他学识浅陋,反说:“对,对,我记起来了,是《冯子家语》里的话,它的意思是…”
冯淼见他那种不懂装懂的样子,实在好笑,忍无可忍,就大声说:“意思是不通,不通!”
这回楚景春可懂了,脸立时红涨得像块猪肝,说:“不通?哪里不通?”
“老兄,请问这“红”花,怎么会“紫”一片呢?”
楚景春瞪着眼睛说:“怎么不能‘紫’一片?常言道,红得发紫嘛!”
冯淼也不跟他争,接着说:“我问你,芳草怎么绿得像麻,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亏你自命为当今李白,你就不记得‘燕草如碧丝这一句吗?他既能说“如碧丝’,我就能说‘绿如麻”,丝麻不都是一根根,一缕缕的,有什么不行?”
“再问你,这‘春光坏’像什么话?”
“既能说‘春光好’,就能说‘春光坏’!”
“这‘打掉大门牙’也能上诗吗?岂不吓死活人?”
楚景春红涨着脸说:“这叫‘语不惊人死不休’”两人越说越僵,楚景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冯淼见他走了,想着他那首臭诗,笑着走进内室。刚想跟十四娘学说一遍,见十四娘满面愁容,忙问:“你怎么了?”
十四娘说:“刚才你们争辩,我都听见了。我早说那个楚公子不是善类,他家又有权势,你这样讥笑他,他能够善罢甘休吗?到那时候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冯淼仔细一想,十四娘说得很对,连忙认错,并且说一定设法挽回。
不久,冯淼去参加了府考,文章写得十分得意。谁知发榜之后,名列第二,头名却是楚景春。这分明是考官要讨好楚通*使,冯淼自然心里也明白。这楚最春却沾沾自喜,在他生日那天,大摆酒筵,特意派人去请冯淼,为的是当众丢冯淼的面子。
冯淼本想不去,又怕把事情再度弄僵,只好前去赴宴。酒过三巡,楚最春把自己的试卷拿了出来,让大家传看。宾客们自然是赞不绝口。楚景春乘着酒兴,对冯淼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以为这次我能名列老兄之上,恐怕就因为这起首几句要略高老兄一筹吧?”话刚落音,满座又是一片赞扬之声。
这时,冯淼已经有了八分醉意,早忘了十四娘的嘱咐。一听这话,先是冷笑了一阵,然后说:“哎呀!难为老兄还自认为有自知之明,直到今天,你还以为你那榜上的名字是用文章换来的呀!”说罢,又哈哈狂笑起来。座中谁也没想到冯淼会当众说出这样的话来,登时,全场愕然,不知所措。
楚景春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煞白。有两个机灵的连忙出来打圆场,说冯淼发酒疯了,把他硬拉回家去。一场酒席就这样不欢而散。
冯淼回到家里,清醒了以后,十分后悔,就把当时情形告诉了十四娘。十四娘又急又气,叹了口气说:“像你那样的刻薄话,对君子说是伤了你的德行。对小人说就会害了你的性命。你的杀身之祸不会太远了。我不忍心看你落到那种下场,让我们从此分手吧!”
冯淼哪里肯放十四娘走,一面哭,一面表示悔过。十四娘说:“你一定要我留下,可得依我一件事:从今以后,你闭门谢客,还得把酒戒掉。”冯淼满口答应。
从此,冯淼终日在家读书。十四娘为人十分勤俭,每天在家织布,偶尔也回娘家看看,但从不在娘家过夜。还拿出一些本钱来让老仆冯忠去作些小买卖,把赚来的钱都扔在堂屋门后边那个大闷葫芦罐儿里。有人来访冯淼,十四娘就让冯忠挡驾。楚景春几次派人来邀冯淼,都被挡了回去。
有一天,冯淼的堂兄死了,冯淼不得不去吊唁。谁想在灵堂上遇见了楚景春。楚景春不但不计前嫌,还一定要请他到家里去喝酒。冯淼记着自己对十四娘的诺言,执意不去。楚景春竟然叫手下人拉着冯淼的驴,死乞白赖地把冯淼请回家去。
到了家,立刻摆下酒宴,美酒佳肴,十分丰盛,还有十多个歌姬在席前献舞。冯淼敷衍了一会儿,几次告辞,楚景春都死留住不放。
冯淼自从那次和十四娘约定,已经有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一直滴酒未饮。这时,几杯美酒下肚,酒兴上来了,再加上歌姬们翩跹起舞,颇觉得赏心悦目,也就不再说走了。工夫不大,就喝得醺醺大醉,竟然就倒在座上,人事不知。
五更时候,冯淼才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屋子里黑糊糊的,揉了揉眼睛,就着微明的天色,看出自己是独自睡在一间小书房的躺椅上。他站起身来,仍觉得头昏眼花。看见屋里有一张小床,心想,再到床上去睡一会儿吧!站起身来,刚一迈步,脚下有东西绊了自己一下,差点跌倒。用手一摸,却是个人。心想,这是楚景春派来伏侍自己的书僮,大约他见自己总不醒,也在脚下睡着了。就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想把他叫醒。
谁知,那人一动也不动。冯淼觉得奇怪,就俯下身去,用手一摸,身上是冷冰冰的,再用劲按了接,浑身硬梆梆的,分明是一具死尸。于是,冯淼吓得大叫起来。叫声没有落音,灯火齐明,立即闯进几个家人来。这时,冯淼就着灯光再仔细一看,原来脚下躺着的竟是一具女尸,头上有个碗大的伤口,血迹模糊,下身衣服也被扯破了。家人的立刻揪住了冯淼。
这时,楚景春也跑了过来,看了看女尸,转过脸来,指着冯淼破口大骂:“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我楚景春爱你的才学,把你待为上宾。你竟然敢奸杀我的使女!”立即吩咐家人们把冯淼扭送到邯郸府衙。
那府尹见原告是通*使的儿子,哪里还肯听冯淼的申辩。一百板子打得冯淼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由于人命关天,冯淼至死不肯招认,府尹吩咐把他押在死牢里,次日再审。
消息传到冯淼家里,十四娘泪如雨下,说:“我早就知道有今天哪!”便立即四处去求亲友设法营救。不料,人们惧怕楚家的权势。都婉言推托。十四娘只好派老仆冯忠先带着银子到狱中打点。狱卒得了银子,自然要对冯淼另眼相看。又给他治伤,又给他好的饭菜,还给他铺了个草帘子让他睡。
当天夜里,冯淼由于臀部伤口疼痛,趴在稻草帘子上,悔恨交集,睡不着觉。忽然闻到一股兰麝香味,抬头一看,十四娘竟然坐在自己身旁。忙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十四娘低声说:“那你就别管了。”冯淼这时心里说不出的委屈,只剩下抽搭了。十四娘见冯淼被打得血肉模糊,心里就跟刀扎一样,也是泪流满面,对冯淼说:“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明天怕要过第二堂。他们让你招什么,你就招什么,免得皮肉受苦。你放心,我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来。”
冯淼见十四娘说得那样果决,只得点头答应。十四娘又抚慰了冯淼一番,然后走到那铁窗前面,不知怎么一挤,竟挤了出去。分明是从两个看牢的面前走过,那两个人却像根本没看见似的。
再说那老仆冯忠,本是河南内黄县人,六十年前家乡闹水灾,一家人只活下他母亲和他两个来,他那时只有三岁。母子俩流浪到邯郸,无依无靠,在街头讨饭,遇见冯淼的爷爷冯有德。
冯有德见他母子十分可怜,就把他们带回家去。母亲当了冯家的女佣人。冯忠和冯淼的父亲同岁,主仆俩是从小打打闹闹在一起长大的。所以冯忠除了这个家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自己的家。冯淼这一成亲,乐得他合不上嘴。冯淼这一吃官司,急得他老泪纵横,饮食俱废,恨不得替小主人去坐牢。十四娘让他去观察楚家的动静。他便装扮成一个乡下老头,在楚家门口徘徊。
出事的第二天,见楚家几个家人抬出一个芦席卷儿来,说是那使女的尸首,要抬到城外去埋。冯忠就远远地跟在那帮人后面。到了城外乱葬岗子上,那帮人把席卷儿往那儿一撂,扭头就往回走。路经一家酒店,那帮人便进了酒店。冯忠也跟着进去,就在他们邻近的桌旁坐下。
这帮人里有个黑大个儿,看样子是个头儿。就见他一面喝着酒,一面说:“哥儿们,今天咱们可得多喝几杯,驱驱这股子邪气!”
另一个人说:“死个把人有什么邪气呀?”
黑大个儿说:“什么?没有邪气?你说这丫头死得冤不冤?”
另一个人说:“冤是冤,没让那小子糟蹋了,落个清白身子就算不错。”
黑大个儿一听,哈哈大笑,说:“糟蹋!你还他妈蒙在鼓里呢!”
这些人一听,这话出有因,都争着追根问底。黑大个儿先是卖关子,后来酒劲上来了,就沉不住气了,说:“我说可是说,第一,这顿饭算你们大伙请我。第二,可不许告诉别人。”
说着,看了看四周,别的桌子都空着,只有冯忠就在旁边桌旁喝酒,他犹豫了一下。冯忠见机行事,立刻站起身来,操着河南口音对那帮人说:“列位大哥,我是从河南来投亲的,跟你们几位打听。这邯郸府有个三官庙吗?”
黑大个儿说:“有。”
冯忠装着耳聋,故意侧着耳朵,凑过去说:“啊?有吗?”
黑大个儿见他聋得那样子,心里烦了,在他耳旁大喊了一声:“有!”
冯忠装出勉强听见的样子,说:“有啊!请问要上那儿去,怎么走哇?”
黑大个儿趴到他耳根子上大吼着说:“进城,路南,头一个门儿!”
这伙人一听,全都哈哈大笑,有人就说:“对,把他支到棺材铺里去,他不就是现成的棺材瓤子吗?”
冯忠还装着凑合能听明白的样子,把黑大个儿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啊,进城,路南,头一个门儿。”说罢还连连道谢,那伙人又是一阵大笑。冯忠便又坐下来喝酒。
那伙人见冯忠又老又聋,又是才由外地来的,也就不放在心上了。于是,黑大个儿便放低了声音对大家说:“告诉你们,那丫头不是冯淼害死的。”
“那是谁?”
“是咱们大奶奶!”
“那是她陪嫁过来的贴身的丫头,她干嘛要打死她?”
黑大个儿一笑说:“你们真糊涂!咱们大奶奶那股醋劲儿你们还不知道?府里的丫鬟有敢搽胭脂抹粉的吗?听说咱们大爷对这个丫头有点意思,这丫头心里也明白。那天大爷睡午觉,把被掀开了。这丫头过去给他盖被,让大奶奶瞧见了,抄起一块砚台,照后脑勺就这么一下,当时就没救了。
大爷醒了也没敢吭声,就叫我先把尸首塞到书房床底下。前天冯淼让大爷灌醉,送到书房。大爷又让我把尸首拉出来放在冯淼脚眼前,还把下身的衣裳扯了个乱七八糟,这回就算有人给她偿命了。”大伙一听,全都愣了。
黑大个儿说:“愣什么?没咱们哥儿们什么事儿。来来来,这杯酒咱们一祭天地,二祭死*,心到神知。冤有头,债有主,找不到咱们头上来。”说着,举了举杯,把酒撒在地上。接着,这伙人便又畅饮起来。
冯忠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赶紧付了酒钱,回到家里,禀告了十四娘。十四娘说这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当天就见十四娘派丫鬟香宜出了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这天,冯忠到狱中送饭回来,见门口石阶上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面黄肌瘦,蓬首垢面,衣衫褴褛。过去一问,原来她名叫禄儿,是从河南逃荒到这里来的。
冯忠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身世,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就把那姑娘领到家里,见了十四娘,想让十四娘把她收下当个丫头。十四娘上下一打量这姑娘,便吩咐带她去洗洗澡,换换衣服。姑娘洗漱完毕,又来见十四娘。十四娘这时一看,只觉得眼前豁然一亮。
那姑娘发似乌云,肤如凝脂,身材五官无一处不长得恰到好处,特别是那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目光一闪,不用言语,就已诉尽了无限的哀怨。十四娘从心里爱上了这个姑娘,当即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黛秾,把她留在身边,暂时顶替香宜。这还不算,平日待她可说跟姐妹一样,连冯忠都纳闷这两人哪里来的这样的缘分。
再说这天,冯忠又到狱中送饭,狱卒告诉他冯淼的罪已被判为绞刑,就等秋后处决了。冯忠一听这话,一路哭回家来,见了十四娘,已是泣不成声,好容易才把这凶信说明白。不料十四娘听了声色不动,只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你下去歇息吧!”弄得冯忠莫名其妙。以后,就再也没见她提起这件事。
冯忠不免暗暗埋怨起来,暗说:“这哪里还有点夫妻的情意!”
春去秋来,眼看要到处决的日子了。冯忠见十四娘有些变样了,整天焦躁不安,饭量大减。有时还见她暗暗擦眼泪,有时深夜不睡。
有一天,丫鬟香宜忽然回来了。冯忠见十四娘和香宜悄悄地说了半天。说完以后,立刻笑容满面,一切如常了。
过了一天,冯忠探监回来,见了十四娘,老泪滂沱,说冯淼要十四娘到狱中去见最后一面,次日就要处决了。不料,十四娘只“嗯”了一声,连眼圈也没红一红,看来也不想到监狱里去。
冯忠直气得血往头上涌,浑身发抖,实在忍无可忍,竟然指着十四娘说:“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家少爷怎么样待你,他如今含冤负屈就要归天了,你倒像没事人一样,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你不去,我去!我得给少爷去喊冤!”说着,疯了似的闯出大门。
冯忠刚出了大门,迎面撞上一群人,都是街坊邻居。人们见了冯忠,纷纷说:“道喜,道喜!”
冯忠一时蒙了头,看样子人们不像是说反话,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说:“你还不知道哇?楚景春他爹被罢了官,道台大人奉旨到邯郸府给你家少爷翻案来啦!”
另一个说:“听说是楚家杀了人,诬赖你家少爷,楚景春夫妇俩全给抓走了。”
冯忠一听欣喜若狂,踉踉跄跄跑到府衙,果然冯淼被放了出来。
冯淼回到家里,见到十四娘,夫妻抱头痛哭。冯忠却在一边生气,嘴里嘟囔着说:“这会儿又来这一套假招子!”
冯淼问十四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怎么知道我的冤枉呢?”
十四娘擦干眼泪,一指香宜,笑着说:“你问她吧!”
原来,自从冯忠把楚家如何打死使女,如何嫁祸于人的情形告诉十四娘后,十四娘想,楚景春的父亲官高势大,不告到皇上那儿去,别想翻过案来。
当晚,便让丫鬟香宜上北京告御状。香宜和十四娘同属狐类,本想靠自己的神通,定能直入宫闱。谁想到了紫禁城下,才看见宫廷四周都有神灵守护,*狐之类无法靠近。
她围着御河转了好几个月,也找不到个机会,心里又怕误了事情,正想回家与十四娘再想办法,忽然听说皇上要驾幸大同。香宜急忙先赶到大同,装作走江湖的歌女,在皇上扮作商人四处巡游的时候,香宜上前见驾。
皇上见她能认出自己来,已经是惊异万分,又见她长得艳如桃李,那时粉泪阑干,恰似一枝带雨的梨花,心中又是喜爱又是怜悯,便仔细听了她的申诉。香宜冒称自己是生员冯淼之女,把冯淼被诬陷的情形哭诉了一遍。皇上大怒,立即传旨将楚景春之父罢官,并责成当地官员彻查冯淼冤案,还赏了香宜黄金百两。
冯淼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不由得感激涕零,也不顾主人的身份,急忙向香宜拜了几拜,谢香宜活命之恩。香宜说:“如果不是少奶奶出主意,我哪里懂得告什么御状。”
冯忠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十四娘。这时,十四娘又让黛秾上前拜见主人。冯淼一见黛秾,一时被那秀丽超尘的姿色惊呆了。心想:怪呀,我活了这二十多年,在遇到十四娘之前,以为世上本没有什么西子王嫱。见到了十四娘,知道自己错了。但认为十四娘之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怎么今天又遇到一个绝代佳人,简直和十四娘难分上下。虽是如此,他却毫无非分之想,说:“你就安心在我家住下来吧!以后有了你家人的消息,我就送你去和家人团聚。”
经过一场患难,冯淼这一家人,夫妻、主仆之间情深无限,欢欢喜喜地过了些日子。一天,十四娘突然对冯淼说:“我本属狐类,蒙你错爱,我感激不尽。经过这一场风波,我深知人情险恶,不想久留尘世了。今后,黛秾可以替我服侍你,我们就此告别吧!”
冯淼一听这话,惊得半响说不出话来,接着,放声大哭,拜倒在地上,拉着十四娘的衣裙,死也不肯放手。十四娘见他这样,也是心中不忍,只好叹了口气,说:“好吧,那我就再留些日子。”
自从冯淼出狱回家以后,卧房中的事十四娘都交给了黛秾。这天晚上,冯淼困倦了倒在床上昏昏欲睡;见黛秾始终站在床前侍候着,又总不见十四娘进房来,便对黛秾说:“你去请少奶奶来安歇吧!天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只见黛秾局局促促,显出为难的样子,心里十分奇怪,忙问是怎么回事。黛秾腼腆地低声说:“少奶奶不到房里来了,让我服侍您……”
冯淼这才明白十四娘收留黛秾,并且给她取了这个名字的深意。黛秾就是代侬(我)。原来十四娘早就想好让这姑娘代替自己,和冯淼白头偕老。冯淼这时对十四娘又是爱,又是怨,心中别是一番滋味。便对黛秾说:“难道你也愿意?”
黛秾说:“少奶奶待我恩同再造,按说她让我干什么我都不应违抗。不过,让我做这件事,我总觉得对不起她,我真左右为难哪!”
冯淼明白黛秾的心意,说:“好姑娘,你想得对,我和你都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情。你表面上听她的话,我们永远兄妹相待,你愿意吗?”
黛秾听了,脸上立刻现出笑容,说:“哥哥,妹妹给你行礼了。”冯淼连忙把她搀起来。
那夜,冯淼硬使黛秾在床上睡下,自己就在躺椅上过了一夜。其实,十四娘又不是凡人,冯淼和黛秾哪能骗得了她,但她却装作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冯淼见了十四娘,忽然感到她变了样子。脸上起了不少皱纹,面色变黄了,眼光黯淡了。
又过了一个月,十四娘乌黑的头发却白了大半。再过一个月,十四娘脸上生出一片片的黑斑,牙齿一颗颗地脱落,背也驼了,连声音都变得沙哑不堪,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太婆。
尽管如此,冯淼对她的情意没有丝毫改变。没有多久,十四娘病倒了。冯淼日夜在床前服侍,不怕累不怕脏,就像对待父母一样。不到半个月,十四娘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后来竟是滴水不进。
临终的时候,眼睛直盯着冯淼,手直指着黛秾。冯淼见十四娘咽了气,只哀嚎了一声,便晕倒在地上。
十四娘的丧事办得十分排场。安葬之后,便忽然不见了香宜。黛秾为冯淼料理家务,家里立着十四娘的灵位,两人始终像亲兄妹一样在一起生活。
冯淼只会读书,既不会经商,又无力务农。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兄妹正在发愁的时候,忽然想起堂屋门后边那个大闷葫芦罐儿。走过去顺上面的小孔用筷子捅了捅,硬得捅不进去,用斧头一砸,罐子破了,哗啦一声,金子银子摊了一地。从此,冯淼的家道便富裕起来。
后来有一天,冯忠出外办事,路经太华山,猛然间,看见十四娘骑着一头青色骡子缓缓地走来,香宜骑着小驴跟在后面。十四娘见了冯忠,关切地问:“冯郎好吗?你转告他,我们都已经成仙了。”说完,挥手告别,仍旧缓缓地向西走去。
冯忠悲喜交集,想要上前拉住牲口,不知怎么两腿软绵绵的,无论如何迈不开步,喊也喊不出声来,眼看着两人的影子消失在云雾苍茫之中。
结语:如果您看得满意,喜欢这个故事,不妨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