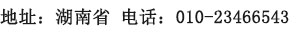文
沈西城
日本留学期间,校方处理不善,未能入住宿舍,要花钱到外面租房子,结识了不少好邻居。
在银座、新宿、涩谷浪了大半个月,学校开课。早上有微雨,偕同岩本先生跑到大久保的国际学友会报到,转进小巷,徒步十分钟左右,便到?。一瞧,呆住:这就是驰名国际的日本语学校吗?哪有丁点儿名校气派?且看它的模样儿吧!两、三栋二层矮楼挤在一起,灰墙土瓦,沉沉郁郁。庭院里,栽著几棵客松,伸著桠枝直插灰灰天穹,隐约展示出不屈的姿态。趋近看,楼墙剥落,露出土砖。呀!横看竖看,都不能称作是名校啊!在来日飞机上,我闭上眼默想著将要进去学校的面目:校舍巍峨宏伟,庭园绿草如茵,多少沾上我深深爱慕的明治古风吧!可眼前的名校,跟想像的,相差忒远了。
走进门,先到校务处登记,接待我俩是一个老女人,一口标准江户日本语,听不懂,要劳岩本先生一一转述。入学手续迅速办妥,老女人打量我一下:“叶桑,下周三你就可以来上课。”欢喜若狂,打下周三起,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日本留学生了,我甚至愉快地想到将会能讲日本语、看懂日本书。正自兴奋之际,耳边飘来岩本先生的传言,有如一杯冷水照头淋,把我从美梦中催醒过来。岩本先生跟老女人的对话,相隔五十年,仍然记忆犹深。
岩本:“周三入学太好了,请问寮(宿舍)准备好了吗?”
老女人:“岩本先生,这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寮已满员(满)了,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
岩本:“不是早准备好的了吗,现在怎会没有了?”
老女人:“时序出现了问题,叶桑申请的文件迟了些日子到我们这里,收到时已过了两天,只好把宿舍转给台湾学生。”
岩本怒道:“这有点儿过分了吧!怎搞的,两地文件邮递上的误差,你们是应该知道的!”
老女人毫不退让:“我们学校一向照本子办事,我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有个屁用!岩本急得跺脚。我不懂日语,察言辨色,多少看出端倪,我对岩本摇了摇手,示意我们回去。归途上,不住向我说对不起,反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事已如此,只好自家想办法。香予伯家里人多不便住宿,只好另觅居停,那就得多花钞票。香予伯代打电报去香港,母亲仅回复二字:“租吧。”于是托不动产代办,岩本担保,在世田谷区松原明大前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六席小房,倒也雅致洁净,灰色木墙,赭红门户,红白双映,整齐悦目。
门前垂柳数株,迎风招展,人家屋檐挂有风铃,微风拂过,荡起清脆声响,涤人心胸。一看便合意,决定租下来,房租一万五千不便宜,台湾同学在下北泽租得同样一间六席小房,租金只八千,足足贵了差不多一倍,贪图享受安逸活受罪。母亲疼我,把每月生活费用调高至三万,去了房租的一半,剩下万五,东京物价高,入不敷支,只好勒紧肚子度日。
明治大学前车站一带,喧闹非常,满是戏院、酒吧、超市、餐馆,购物吃食方便。东京名闻世界,食物却差,我这个香港学生吃不惯生冷东西,人人视为美味的寿司,我难吞咽,惟有吃拉面,浮游于汤面那两三片瘦肉,纤弱得风也吹得起,咋吃?不吃面,只好吃咖喱饭,甜甜得毫无辣味,用竹筷挑,翻江倒海,不易找到一两块肉,可幸有味噌汤,勉能进口,倒是伴在饭边的蔬菜,蘸上沙律酱,清爽好吃。偶然 一点,来一碟炸猪扒饭,已是食福无边。日本的米饭黏黏糯糯,入口甜,却易坏牙,因而日本人多有齿疾。
我自出娘胎儿以来,不曾独居,凡事都有佣人代劳,来到东京,孑然一身,大少爷什么都要自己做,洗衣成了我最头痛的事。隔邻田中太太有洗衣机,免费代洗,盛情至可忻感;对门的川崎大姊,隔三岔五送上一些草饼、蛋糕、便当给我裹腹;还有中村老婆婆,背脊微佝,步履蹒跚,每早必叩家门,叫著“叶桑,你元气(好)吗”?答曰“元气”,就转身离开。开门一看,嶙峋背影影渐渐消失眼中。当然忘不了我的日本谊母冈田寿子,老太太每个星期必招我家里夕食(晚饭),知我不吃鱼,代之以牛柳。牛柳在日本是贵价货,一般人家都吃不起。九四年回香港后,我每吃牛柳,鼻子一酸,都会想起冈本妈妈。
七八年重回松原,旧居已租予一对青年夫妇,老婆婆归长野故里,田中一家早已他迁,冈本妈妈则于我离日三年后,一病不起。漫步至明大前车站,华灯初上,我常去光顾的阿菊小酒馆门庭依然,金发红唇、有“明大前青江三奈”称号、妖娆的玲子妈妈生却已不知去向。玲子,可还记得那个夜,檐前滴雨,风吹暖帘,我在店里听你唱著青江三奈的《国际线待合室》:“蓝色灯光的飞机引行道,不知为何今日会感触良深,相见是痛苦的,相见是痛苦的,明知道是这样,仍然还是独自前来,想见你一面……”此刻我欲守在人行道上见你一面,你会来吗?
版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文章,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本文文字内容未经授权严禁非法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