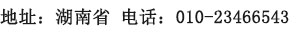白癜风治疗权威医院 http://www.znlvye.com/第23期作者艺术家:段建伟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在巩义鲁庄后林为什么画农民?11月底的一个傍晚,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坐在豫西的一个土坡上歇脚。一座座房屋从近处稀稀疏疏地向远处散开。高处的房子,被夕阳抹上了红色。玻璃窗和瓷片闪动的光芒,像高音键敲出来的声音,高吭而暸亮,一下子就会钻到你的心里。磨房的机器停顿的时候,能听见远处像是吵架的声音,偶尔激越一下也就中断了。也有炊烟慢慢散到空中。一个荷锄者从身边走过,直直地就盯了你,远处坡上的渡槽,在坡顶形成了一个向上的突起,当我被其所吸引心生敬慕和庄严的时刻,一队形神兼备的小猪直扑跟前,不由你就发笑了。我的朋友就说,这真是个好地方。在巩县鲁庄后林的一个坡道上,迎面一个吃力地推着自行车的少年的目光与我不期而遇,让我蓦然觉得这个陌生的生命和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的眼睛曾经被木偶戏前台的热闹所吸引,却没想到过那双诡秘灵巧的手。一些儿时生活的片断,我无法逃脱的血脉,那些特定的时刻和景致,都一下子清楚地和眼前的东西重叠起来。我重复着别人的提问:你为什么画农民?你为什么画农民?我就又一次地口吃了。迎面一个农民伸出右手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烟。生命的本质几乎就写在这张脸上。它笑着,我迅速被它感染着。这种生命的活力我在别处见过,在一棵树身上,一个湿漉漉的土坡上,一两声鸣叫中,一个动作中,一句省略了的话语中,鲜活自然,直接而有力。我看重这些平淡,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景色和几乎无法辨认的表情。我快要看到那双手了,诡秘而灵巧。我被这些平淡的生活吸引。被它的捉摸不定和模糊的含意吸引。我揣摸着和领悟着,有点犹豫地向前迈了一步。我逐渐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用这样的语汇去诉说,他们就用这样的语汇和眼神来回应我。这像是一桩秘密交易,我得到了我要的东西。这种时候,我和他们一样不易察觉地笑了。宋词手艺红衣少年麦客到来英雄像小时候画画,也是拿根棍子或粉笔在地上乱画,遇上宽厚的大人,就顺口表扬我几句,有爱清洁的人碰上了就会吵我弄脏了一片地。当时还没有人教我写字,乱画的瘾就特别大。现在知道了当年王冕也就是这样画出来的。不过王冕画的是荷花,我画的多是日本鬼子和地主,带着恶意把这些形象画出来特别带劲。后来见到儿子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画鬼怪,就想天下的儿童大概都得过这个年龄段吧。有一天父亲很郑重地和我商量,他大概是说,日本鬼子当然可以画,但能不能多画些正面形象呢,比如工农兵。我就接受了父亲的指引,开始照着画书上画英雄。当时画过的我记得有几张杨子荣,有一张一手扯着大衣襟一手向外展开的杨子荣像,我还得意得很。后来上了小学,班主任就让我参加板报小组,有时侯放学以后还让我跟他回家,在他的桌子上画刊头画,那一天就在他家吃了晚饭。那时候学校出墙报很勤,所以就经常有画刊头的机会。三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到了郑州,这以后才开始接触到素描、速写一类的专业知识。当时条件差,铅笔用短了,就用一根小管子套住,还能用一阵子。画速写的纸,好多是母亲拿回来的废报表。同院有个在邮局工作的张姨给过我一卷电报纸,我没舍得用,后来也就忘了。结果前一段收拾屋子,还好好的在那儿放着。月照大沟发烧亲爱的叔叔小孩盆花少女麦秸坪麦秸坪指的是这座山,还是山顶上村庄的名字,我一直也没有问过。每爬一次都气喘,盼着快到那一小片马尾松林子。那是歇脚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吸烟,烟从嘴里一冒出来,风立刻就把它吹散了。麦秸坪是个突兀的山包,四周都平得很,往远处走上一段,才是其它的山包。麦秸坪并不太大,也不高,但它的走势却具备了崇高的气质。它常在我眼前显现,几乎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化身。我却从没有让它在我画面中出现。我喜欢平缓一些的,而它则过于高亢和激越。如果山上有树,我也宁愿是一棵歪脖子垂柳,这样更接近我的性情。老米说过我的画面缺乏张力,我就老想着这回事儿。看着一块一块的庄稼地我就嘟嚷:你给了我情感怎么就不给我技巧呀。我就老想着我温吞的性子和犹犹豫豫的脾气,自卑就油然从胸中升起。老米呀老米,我回去得好好请你一顿,你得好好说说我。确山确山国庆的画老于给我们找了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一条渡槽架在两个山头中间。站在废弃的渡槽上,自己就觉得有了高大的感觉。渡槽下方正好是一条公路穿过。往东起伏着到了县上,往西七拐八拐能通到山西。下午画完两张画,正好是太阳西沉的时候,往东看是暖洋洋的一片,公路上的影子里,就像是蓝色的长带子,到了远处的山上像突然没有了一样。往西看正好被落日刺了眼,地上冒着蒸气,远处公路上的汽车像在水上漂着,不停地晃动着。路边的麦田和果园是两种绿,几颗梨树在前面很好地长着。国庆画的那张顺光的小画,就没有把这些很好的树当树画,我看这房屋和村庄,他也没有把它们当成房屋和村庄。我从这种出奇不意的一击里回过神儿,就又多了种感觉,真觉得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庸俗了。我转回去把这种感觉告诉老于,老于就说这真是不让老同志们混了。我俩就走到国庆跟前,国庆就赶紧让烟,我也没有接烟只是死盯着这张画看。慢慢的车灯就显得亮了。树也像溶到了变成蓝黑的天空里。路上只看见移动的两盏灯,忽一下从我们脚下过去了,然后又是两盏灯。回去的路上老想着国庆这张画,就有点想多了,一会儿就想着自己还得刻苦,一会儿就觉得自己脑子不行了。不过也就是那么一会儿,想起明天店老板要为我们杀猪的事,脚底下就轻快了许多。走路唱歌唱歌背面两少年正渠提起的沟村子东头是条几里长的沟,第一次被正渠领去的时候,沟里已被种上了庄稼,庄稼就和着杂草繁繁茂茂,看不出沟的原样,我也想象不出这条被正渠不止一次提起的沟,二三十年前能给予正渠什么。顺着坡道,小跑着就下到沟底。我想正渠童年所听到的故事,一半都与这条沟有关,而我断断续续的农村生活只给我一些零零散散的回忆,只是一些片断,却没有这样完整的沟。正渠在前边走着,而我却不着边际地俯身拾起一片青花。我后来才确信我们在榆林大沟走着的时候他是怀着和我异样的感觉。在银山界沟里一群人走着的时候,他也一定是这样。这条沟就刻在了他记忆里成为他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他感情的一部分。去年我和国庆下到沟里,国庆在路上就问我说这条沟很有意思是吗,我说是有意思,只是我们看不出意思。我们只在沟底拾了一把瓷片,撒了一泡尿,就走出了沟。母子水库-1水库-2文中部分内容有删减,全文请查阅《画家画语》,辽宁美术出版社年出版。